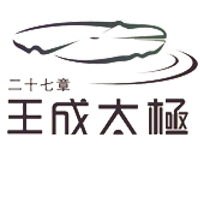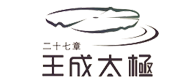传奇轶事
鲁迅和武术、气功——少为人知的重要的史实
鲁迅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他和武术、气功之间有过什么关系?关于鲁迅的评介文章甚多,却少有论及于此的专文。其实,这不仅涉及中国近代体育史,也是涉及鲁迅研究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重要史实。
1. 鲁迅作“杂感”反对“保存国粹”
鲁迅(1881-1936),作为近代最有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虽属“文人”范畴,却和中国最传统的体育--武术、气功有过某种联系。
“五四”运动时期的鲁迅,是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激进战士。此后,他在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写了不少杂感,直接抨击社会弊端、激烈反对封建旧传统。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辛亥革命后虽成立了中华民国,却没有根本动摇统治中国二干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封建旧思想、旧传统依旧形成一种强大势力,以排斥和抗拒外来思潮及进步思想。社会上遗留下来的许多旧现象触目皆是:尊经复古、崇道劝孝、尊孔读经,甚至以儒家名人鼓吹参禅养性而大做其“迎尸拜蛇、扶乩炼丹”的法术(如“同善社”之类会道门)……鲁迅对此深恶痛绝,认为:“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道路。”
(1)尖锐而激烈的社会批评成为鲁迅早期杂感的待色,“国粹”和旧文化是他主要抨击目标。
鲁迅说他的杂感“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2)“国粹家”觉得“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3)鲁迅反对旧文化、旧传统的立场很坚定,激昂宣称:“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4)
于是,作为国粹的静坐养生法就成为鲁迅一个目标了。
2. 提倡“静坐”养生的因是子
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一位因练功而有极大影响的人物蒋维乔,别号“因是子”。
这位因是子是江苏省常州人,生于清朝道光十一年(1827),出身于书香门弟。他幼年体弱多病,用他的话说是“自幼多病、消瘦骨立,父母虑其不育。年十二即犯手淫、久之梦遗、头昏、腰酸、目眩、耳呜、夜间盗汗……百病环生。”他也曾“百般求治疗之法”,皆无效验,于是在20岁以前就开始研究静坐练功法,一连坚持了十八年,“不特病疾竟瘳,而精神日益健康。”后来他谈到日本人冈田虎二郎、藤田灵斋等著的《冈田氏静坐法》、《藤田式息心调和法》等书,又听说这些书“风行一时,重版皆数十次”,那两位日本气功师的门徒万万千千,影响甚广。因是子先生遂慨然浩叹道:“是我国固有之术也!”他认为冈本和藤田所倡导的静坐法并没有什么奇持的地方,也是根据中国古代医学、养生、武术等理论而写成。但是日本人能运用近代科学的道理来解说静坐法的道理方法,不含神秘色彩,却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
因是子先生又慨叹道:“察吾国民间习尚,凡一切学术以及百工技艺,苟有超绝恒理者,往往自观为秘法,不肯示人”,以至中国许多绝技都失传了。而我们东边的邻居则不是这样,“凡得一术,必共同研究之,其结果远胜于我,我国且转而取法之矣。”比如明朝末年中国武师陈元赟流亡日本,向一些日本人传授了中国武艺。结果日本人据此加以研究而丰富,造成了当今日本国技“柔道”,而中国的摔角技艺仍然如故,停滞不前。固是子先生接着唏嘘长叹道:“我国之拳术如故也!内功粗者可以祛病,精者乃可成道。然亦以自秘之故,不肯共同研究。彼国人自大学讲师、学生等人,老幼男女起而学静坐法,且学校列为课程,大学生有联合组织静坐会者。嘻!何其盛欤!而我国人则何如也夫?因自秘之故,濒于失传,亦可叹矣。”这位因是子先生遂奋而著书,写了一本《因是子静坐法》,于民国三年(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这本书一扫神秘怪异之谈,“而以心理、生理之学解说之,凡书中之言,皆实验所得。”此书问世后,受到各界人士极大欢迎。据因是子自己说:“书出版后,购者络绎不绝,近则各省,远至南洋,无处不有学习之人”、“此书行销数十万册”。因是子先生也被聘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江南各地学校演讲“静坐法”,影响很大。
这位蒋维乔民国初年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也是鲁迅以不屑口气斥为“那班教育家”之一;加上他又竭力提倡“国粹”之一的静坐养生——这自然成了鲁迅《杂感》中的一个目标。
3.鲁迅反对 “天眼通”等
谈到鲁迅对“静坐”要发“杂感”之前,不妨先谈谈鲁迅对另一“国粹”——中医的态度,因为中医同中国武术气功养生法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
在鲁迅的早期著作中,有不少是不相信和反对中医的。这是因为他父亲死于中医中的“庸医”之手,加之鲁迅又曾学习现代医学(西医),故而他对中医常有贬词。如他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学习西医以后,“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中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内经》一书不但是中医的经典著作,也是武术养生学理论基础,但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却明确反对道:“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竞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学的宝典……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所以他只相信西医:“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
鲁迅不相信中医,更不相信静坐养生。蒋维乔在《因是子静坐法》的《原理篇》中运用了一些中医术语如“丹田者亦名气海”等;在他译述的日本铃木美山所著《长寿哲学》的《病之原因》一节中,引用了德国科荷 博士吞食细菌而不生病的事,来证实精神能影响人的生理功能、静坐调神能强身祛病的道理。这引起鲁迅的强烈反对,在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杂感•三十三》: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
以今天眼光看来,鲁迅所指责的那位“大官”(指蒋维乔)的话并无大错,说不上是什么“鬼话”和“带了妖气”。由胚胎出生为人前不是靠脐带维系生命的发育吗?蒋维乔试图用现代科学阐述人体某些部位很重要的原理,虽不一定十分精当但未必就是“最恨科学”和在“捣乱”。如按鲁迅说法,中国医学中经络、穴位学等基本理论就全是“鬼话”、“妖气”。
在这篇杂文里,鲁迅对一个据说有“天眼通”(相似于现在所说的特异功能)的“神童”的批判,却基本上是正确的。
原来当时山东历城有个叫江希张的小孩是个“神童”,有先天“神通”(特异功能)。传说他不到10岁,就著了《四书白话解说》、《息战》、《大千图说》等书。他在《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中说他有“天眼通”(遥视遥测的特异功能),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能看见宇宙中其它星球的情形:“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他“天眼通”看到的宇宙情形是怎样的呢?在他书中写道: (5)“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压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 君居焉。”
这个叫江希张的“神童”的“天眼通”,和现在一些自称能和“玉皇大帝”、“观世音”交流“宇宙语”的“特异功能者”之类颇有异曲同功之妙。《大千图说》于1916年出版,作者在书中说他“创立三千大千世界之说”,是鉴于“近来物质家,创无天帝鬼神之说,一时靡然从风,不知其贻害之大,将有使全球民物同归于尽者”。他还扬言:要使“天下人人莫不敬天畏天”。这段话,更简直同近年一些新编“气功”的“鼻祖”、“大师”们声称的“到了21世纪世界将毁灭”,只有人人都练他(她)那家气功才会拯救人类的论调如出一辙。
那个“神童”江希张被国内外的守旧势力所广为宣传,美国的李佳白还以“万国道德总会”名义出版了“神童”著的《息战》一书,并为该书写序,称他“具天纵之姿,有卫道之志”,“以一童子而能融洽教理,为世界民族请命”。
所以鲁迅在嘲讽蒋维乔的静坐养生法后,又辛辣地在《杂感•三十三》中写道:“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鲁迅对此作了许多批判。
据说,这个“神童”所谓10岁著书的特异功能都是假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等书都是他父亲江钟秀和别人代写的。(6)
近年来,有人认为有关气功及特异功能的争论只是解放后的事,以上事实说明并非如此,说明早在80年前就有对“伪科学”的批判。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反对静坐养生的并不仅鲁迅一人。《新青年1917年4月1日在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一篇《体育之研究》中就有一段话:
“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即毛泽东。
1920年1月长沙《体育周报》特刊第二号有篇《辟静坐》,更激烈地写道:
“静坐的最大害处,就是使人趋于消极,我们一天天的习静,清心寡欲,就一天一天把进取心消磨了……这样子的静坐,即令能祛病,能延年,也不过替我们中国多造一些人类的寄生虫,和社会的蟊贼……”
如果说毛泽东对“静坐养生”的批判,还主要从运动形式(动和静)出发,这篇《辟静坐》则纯粹把运动方式“无限上纲”到政治批判上,已很像文革时期“火药味”浓浓的“大字报”了。
虽然鲁迅、毛泽东等人都曾反对静坐气功,但中国许多人仍坚持静坐锻炼,当时的一些高等学府还成立师生组成的“静坐会”(相似于如今的健身俱乐部、协会)。静坐法流行不衰,许多提倡新文化的斗士也靠它祛病强身。比如郭沫若,他因年青时治学过勤患严重神经衰弱,形销骨立、夜不能眠,痛苦得几乎自杀。百药无效之时他坚持静坐练功,结果顽疾痊愈。静坐法的奇效使他多次浩叹道:
“从前眼前的世界只是死的平面图、到这时候才活起来,成了立体。”“静坐于修养上是真有功效,我很赞成朋友们静坐。我们以静坐为手段,不以静坐为目的,是与进取主义不相违背的。”(7)
这种见解,比之鲁迅等人偏激批判无疑公允得多。
4.鲁迅反对中国拳术(武术)
鲁迅反对静坐养生的同时,还明确反对另一国粹--中国拳术。原来,当时提倡武术者中,除了众多武术家外,还有许多爱好武术的当权者。如马良(又名马子贞),回族人.民国初年任北洋皖系军阀中陆军第四十七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后任济南镇守使。他甚好武术,自己创编了一套技击术,包括了摔角、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并将其用于军队训练中。马良竭力提倡“国粹体育”,曾说;“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新武术者。”他倡导要将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成“新武术”,使之成为“我国之国粹”。他认为欲使武术发展普及,还应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以发扬武德、武风。当时的北洋政府和一些教育家(如章士钊、蔡元培等)对此很赞赏,将它列入中等以上学校的“体操课程”,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国会还通过了把“新武术”定为全国“学界必学”之“中国式体操”的决议,以利普及,成为教科书。在一些高等学府还成立了武术组织,如北京大学就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倡导支持下成立了“技击会”,师生中参加者甚多。
鲁迅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1918年11月1 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杂感三十七》,以他特有的辛辣笔调嘲讽道:
“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地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
鲁迅很反对“竭力提倡打拳”者认为可将“新武术”用于“体育上”和“军事上”的观点。鲁迅认为;“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验’”。因此他反对将打拳用在“体育上”,嘲讽“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须改习本国式体操(打拳)才行”的说法:“无如竞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拷’那些把戏了”。
鲁迅对打拳可用在“军事上”尤为反感。他又嘲讽道:
“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领袖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种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蠢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 (8)
鲁迅认为“清朝末年(1900年)“满清王公大臣”提倡打拳(如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支持义和团广设拳坛,结果后来是“完全失败了”。更何况“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所以鲁迅反对“打拳”能用在“军事上”的说法。
鲁迅也反对提倡、普及武术这一“国粹”,他在《杂感六十四》上再次尖刻地写道:
“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大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 ‘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桩腿’、‘潭腿’ 、‘戳脚’,什么 ‘新武术’、‘旧武术’,什么 ‘实为尽美尽善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筋力,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 (9)
认为传播中国传统体育武术,是“互害”--鲁迅这一立论今天读来是颇使人吃惊的,无疑很有点偏激、过“左”的味道。
鲁迅对武术界内部的争论更加以嘲讽。山东人王讷(众议院议员)曾提出“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提倡改革武术使之成为中国式体操,此议案于19l7年3月22日经众议院通过,而一些热爱传统武术者(如中华武土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会使武术这一国粹的特色丢失。(本文作者注:这种情况,很像现在“官方武术”如“自选拳”、“国家规定竞赛套路”等与“民间武术”争论的情况。)鲁迅讥讽这是“同业的内讧”:
“但总觉现在时势不很太平,无论新的旧的,都各各起哄:扶乩打拳那些鬼画符的东西,倒也罢了……””北京议员王讷的提议推行新武术,以‘强国强种’;中华武士会便率领了一般天罡拳阴截腿之流,大分冤单,说他抑制暴弃祖性相传之国粹”……(10)
鲁迅对武术这一“国粹”的讥讽反对是否正确呢?这里且先不讨论。只须说出的是,当鲁迅那篇《杂感三十七》一问世,立即有人力加驳斥。驳斥者并非鲁迅讥讽的“那一班”提倡打拳的“教育家”,而是热爱武术的武林中人。5.武术家陈铁生撰文驳斥鲁迅
鲁迅于1918年参加《新青年》的编辑活动并成为重要撰稿人。他在1919年发表《随感三十七》后,《新青年》杂志即收到署名陈铁生的一篇驳斥文章:《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鉴于这个陈铁生是近代武术史上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后文将谈到),而他这篇同大文家鲁迅“打笔墨官司”的文章却极少有人提及,这里全录此文、对研究陈铁生及武术史非常有益。请看原文是怎样驳斥鲁迅的:
鲁迅 君何许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个青年。但是这位先生脑海中似乎有点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不过鲁迅 君可曾见过“拳匪”?若系见过义和团,断断不至弄到这等糊涂。义和团是凭他两三句鬼话,如盛德坛《灵学杂志》一样,这些大人先生方能受他盅惑;而且他只是无规则之禽兽舞。若言技击,则身、手、眼、步、法五者不可缺一,正所谓规行矩步。鲁 先生是局外人.难怪难怪。我敢正告鲁 先生曰:否!不然!义和团乃是与盛德坛《灵学杂志》同类,与技击家无涉。义和团是鬼道主义,技击家乃人道主义。(以上驳第一段)
现在教育家主持用中国拳术者,我记得有一位蔡子民(即蔡元培)先生,在上海爱国女校演说,他说;“外国的柔软体操可废,而拳术决不可废。”这位老先生,大抵不是满清王公。当时我亦不以为然。后来我年近中旬,因身体早受攻伐,故此三十以后,便至手足半废。为一位医学博士替我医了两三年。他说,“药石之力已穷,除非去学柔软体操。“当时我只可去求人教授。不料学了两年,脚才好些,手又出毛病了;手好些,脚又出毛病。卒之有一位系鲁迅 先生最憎恶之拳术家,他说我是偏练之故;如用拳术,手足一齐动作,力与气同用,自然无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我为了身体苦痛,只可试试看。不料试了三个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鲁 先生之所谓“拳匪”,居然饮得,食得,行得,走得;“拳匪”之赐,真其不少也。我想一个半废之人,尚且可以医得好,可见那位真真正正外国医学 博士,竟输于“拳匪”,奇怪奇怪,(这句非说西医不佳,因我之学体操而学拳,皆得西医之一言也;只谓拳术有回生起死之功而己。)这就是拳术的效验。至于‘武松脱拷”等文字之不雅训,是因满清律例,拳师有禁,故此缙绅先生怕触禁网,遂令识字无多之莽夫专有此术,固使至尊无上之技击术黯然无色;更令东瀛“武士道”窃吾绪余,以“大和魂”自许。且吾见美国新出版有一本书,系中国北拳对打者。可惜我少年失学,不识蟹行字(按:指外文)只能看其图而已。但是此书,系我今年亲见,如各先生要想知道美国拳匪,我准可将此书之西文,求人写出,请他看看。(驳原文二、三段)
原文谓“外国不会打拳”,更是荒谬。这等满清王公大臣,可谓真正刚毅之不如。这一句不必多驳,只可将Boxine(此系西文,是友人数我的。)这几字,说与王公大臣知,便完了。枪炮固然要用,若打仗打到冲锋,这就恐非鲁 先生所知,必须参用“拳匪”的法术了。我记得陆军中学尚有枪剑术,其中所用的法子,所绘的图形,依旧逃不出技击术的范围。鲁 先生,这又是真真正正外国“拳匪”了。据我脑海中记忆力,尚记得十年前上海的报馆先生,犹天天骂技击术为“拳匪”之教练者;今则人人皆知技击术与义和团立于绝对反对的地位了。鲁 先生如足未出京城一步,不妨请大胆出门,见识见识。我讲了半天,似乎顽石也点头了。鲁 先生得毋骂我饶舌乎。但是我扳不上大人先生,不会说客气话,只有据事直说;公事公言,非开罪也。满清老例,有“留中不发”之—法;谅贵报素有率直自命,断不效法满清也。
粤人陈铁生。八年一月二十日。
“内功”非枪炮打不进之谓,毋强作内行语。铁生赘(11)
这里有必要将陈铁生的驳斥文章略作归纳。
首先,他反对鲁迅把“拳匪”(义和团)弄神搞鬼的“神拳”,同中国传统武术技击混淆起来,而把中国拳术也斥为“鬼道主义”。第二,陈铁生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坚持认为中国拳术“起死回生”的健身功效远胜过西洋体操,故他极赞同蔡元培的话:“(中国)拳术决不可废”。至于中国武术中有些叫法不“雅驯”(不太科学),是因为满清统治者禁武造成的,因而使中国武术在世界体育中“黯然无色”,而仅得中国武术皮毛的日本武士道反大出风头。
第三,陈铁生反对那种认为已有枪炮就可以不要武术技击术的论调,他认为无论中外,打仗冲锋时技击术总是有实战意义的,因而要求鲁迅“毋强作内行语”。
陈铁生的文章是很尖锐的。此时的鲁迅还没有被认为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12)而《新青年》杂志是最提倡民主、学术争鸣的刊物,故陈铁生的文章很快刊登出来。
鲁迅因之在1919年3月2日又写了一篇《拳术与“拳匪”》作公开“答复”:
此信单是呵斥,原意不需答复,本无揭载的必要;但末后用了“激将法”,要求发表,所以便即发表。既然发表,便不免要答复几句了。
来信的最大误解处,是我所批评的是社会现象,现在陈 先生根据了来攻难的,却是他本身的态度。如何是社会现象呢?本志前号《克林德碑》篇内已经举出:《新武术》序说,“世界各国,未有愈于中华之新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序中的庚子,便是《随感录》所说的一千九百年。可知对于“鬼道主义”明明大表同情。要单是一人偶然说了,本也无关重要;但此书是已经官署审定,又很得教育家欢迎,——近来议员又提议推行,还未知是否同派,—一到处学习,这便是的确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正是“鬼道主义”精神。我也知道拳术家中间.必有不信鬼道的人;但既然不见出头联斥,排除谬见,那便是为潮流遮没,无从特别提开。譬如说某地风气闭塞,也未必无一二开通的人,但记载批评,总要据大多数立言,这一二人决遮不了大多数。所以个人的态度,便推翻不了社会批评;这《随感录》第三十七条,也仍然完全成立。
其次,对于陈 先生主张的好处,也很有不能“点头”的处所,略说于下:
蔡 先生确非满清王公。但现在是否主持打拳,我实不得而知。就令正在竭力主持,我亦以为不对。
陈 先生因拳术医好了老病,所以赞不绝口;照这样说,拳术亦只是医病之术,仍无普及的必要。譬如乌头附子,虽于病有功,亦不必人人煎吃。若用此医相类之病,自然较有理由;但仍须经西医考查研究,多行试验,确有统计,才可用于治疗。不能因一二人偶然之事,便作根据。
技击术的“起死回生”和“至尊无上”,我也不能相信。东瀛的“武士道”。是指武士应守约道德,与技击无关。武士单能技击,不守这道德,便是没有武士道。中国近来每与柔术混作一谈,其实是两件事。
美国新出“北拳对打”,亦是情理上能有的事,他们于各国的书,都肯翻译:或者取其所长,或者看看这些人如何思想,如何举动;这是他们的长处,中国一听得本国书籍,间有译了外国文的,便以为定然宝贝,实是大误。
Boxing的确是外国所有的字,但不同中国的打拳;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不会”。正如“拳匪”作Boxer,也是他们本有的字;但不能因有此字,便说外国也有“拳匪”。
陆军中学里,我也曾见他们用厚布包了枪刃,互相击刺,大约确是枪剑术;至于是否逃不出中国技击范围,“外行”实不得而知。但因此可悟打仗冲锋,当在陆军中教练,正不必小学和普通中学都来练习。
总之中国拳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因为这是小事。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作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所以写了这一条随感录,稍能提醒几个中国人,则纵令被骂为“刚毅之不如”,也是毫不介意的事。(13)从以上鲁迅辨解文章中可看出,因为马良写的那本《新武术初级拳脚科》曾经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而且《新武术》序说过一些肯定义和团利用武术的话如:“世界各国,未有愈于中华之新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所以鲁迅就坚持认为”:1.推广武术便的确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正是‘鬼道主义’精神;2.即使拳术可治病健身,却“仍无普及的必要”;3.即使拳术可用于军事,也“当在陆军中教练,正不必小学和普通中学都来练习”。
总之,鲁迅坚持反对“大有中国人非此(指武术)不可之概”——即不应在中国人中宣传、普及武术这一“国粹”。
1. 鲁迅作“杂感”反对“保存国粹”
鲁迅(1881-1936),作为近代最有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虽属“文人”范畴,却和中国最传统的体育--武术、气功有过某种联系。
“五四”运动时期的鲁迅,是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激进战士。此后,他在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写了不少杂感,直接抨击社会弊端、激烈反对封建旧传统。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辛亥革命后虽成立了中华民国,却没有根本动摇统治中国二干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封建旧思想、旧传统依旧形成一种强大势力,以排斥和抗拒外来思潮及进步思想。社会上遗留下来的许多旧现象触目皆是:尊经复古、崇道劝孝、尊孔读经,甚至以儒家名人鼓吹参禅养性而大做其“迎尸拜蛇、扶乩炼丹”的法术(如“同善社”之类会道门)……鲁迅对此深恶痛绝,认为:“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道路。”
(1)尖锐而激烈的社会批评成为鲁迅早期杂感的待色,“国粹”和旧文化是他主要抨击目标。
鲁迅说他的杂感“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2)“国粹家”觉得“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3)鲁迅反对旧文化、旧传统的立场很坚定,激昂宣称:“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4)
于是,作为国粹的静坐养生法就成为鲁迅一个目标了。
2. 提倡“静坐”养生的因是子
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一位因练功而有极大影响的人物蒋维乔,别号“因是子”。
这位因是子是江苏省常州人,生于清朝道光十一年(1827),出身于书香门弟。他幼年体弱多病,用他的话说是“自幼多病、消瘦骨立,父母虑其不育。年十二即犯手淫、久之梦遗、头昏、腰酸、目眩、耳呜、夜间盗汗……百病环生。”他也曾“百般求治疗之法”,皆无效验,于是在20岁以前就开始研究静坐练功法,一连坚持了十八年,“不特病疾竟瘳,而精神日益健康。”后来他谈到日本人冈田虎二郎、藤田灵斋等著的《冈田氏静坐法》、《藤田式息心调和法》等书,又听说这些书“风行一时,重版皆数十次”,那两位日本气功师的门徒万万千千,影响甚广。因是子先生遂慨然浩叹道:“是我国固有之术也!”他认为冈本和藤田所倡导的静坐法并没有什么奇持的地方,也是根据中国古代医学、养生、武术等理论而写成。但是日本人能运用近代科学的道理来解说静坐法的道理方法,不含神秘色彩,却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
因是子先生又慨叹道:“察吾国民间习尚,凡一切学术以及百工技艺,苟有超绝恒理者,往往自观为秘法,不肯示人”,以至中国许多绝技都失传了。而我们东边的邻居则不是这样,“凡得一术,必共同研究之,其结果远胜于我,我国且转而取法之矣。”比如明朝末年中国武师陈元赟流亡日本,向一些日本人传授了中国武艺。结果日本人据此加以研究而丰富,造成了当今日本国技“柔道”,而中国的摔角技艺仍然如故,停滞不前。固是子先生接着唏嘘长叹道:“我国之拳术如故也!内功粗者可以祛病,精者乃可成道。然亦以自秘之故,不肯共同研究。彼国人自大学讲师、学生等人,老幼男女起而学静坐法,且学校列为课程,大学生有联合组织静坐会者。嘻!何其盛欤!而我国人则何如也夫?因自秘之故,濒于失传,亦可叹矣。”这位因是子先生遂奋而著书,写了一本《因是子静坐法》,于民国三年(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这本书一扫神秘怪异之谈,“而以心理、生理之学解说之,凡书中之言,皆实验所得。”此书问世后,受到各界人士极大欢迎。据因是子自己说:“书出版后,购者络绎不绝,近则各省,远至南洋,无处不有学习之人”、“此书行销数十万册”。因是子先生也被聘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江南各地学校演讲“静坐法”,影响很大。
这位蒋维乔民国初年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也是鲁迅以不屑口气斥为“那班教育家”之一;加上他又竭力提倡“国粹”之一的静坐养生——这自然成了鲁迅《杂感》中的一个目标。
3.鲁迅反对 “天眼通”等
谈到鲁迅对“静坐”要发“杂感”之前,不妨先谈谈鲁迅对另一“国粹”——中医的态度,因为中医同中国武术气功养生法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
在鲁迅的早期著作中,有不少是不相信和反对中医的。这是因为他父亲死于中医中的“庸医”之手,加之鲁迅又曾学习现代医学(西医),故而他对中医常有贬词。如他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学习西医以后,“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中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内经》一书不但是中医的经典著作,也是武术养生学理论基础,但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却明确反对道:“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竞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学的宝典……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所以他只相信西医:“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
鲁迅不相信中医,更不相信静坐养生。蒋维乔在《因是子静坐法》的《原理篇》中运用了一些中医术语如“丹田者亦名气海”等;在他译述的日本铃木美山所著《长寿哲学》的《病之原因》一节中,引用了德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
以今天眼光看来,鲁迅所指责的那位“大官”(指蒋维乔)的话并无大错,说不上是什么“鬼话”和“带了妖气”。由胚胎出生为人前不是靠脐带维系生命的发育吗?蒋维乔试图用现代科学阐述人体某些部位很重要的原理,虽不一定十分精当但未必就是“最恨科学”和在“捣乱”。如按鲁迅说法,中国医学中经络、穴位学等基本理论就全是“鬼话”、“妖气”。
在这篇杂文里,鲁迅对一个据说有“天眼通”(相似于现在所说的特异功能)的“神童”的批判,却基本上是正确的。
原来当时山东历城有个叫江希张的小孩是个“神童”,有先天“神通”(特异功能)。传说他不到10岁,就著了《四书白话解说》、《息战》、《大千图说》等书。他在《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中说他有“天眼通”(遥视遥测的特异功能),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能看见宇宙中其它星球的情形:“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他“天眼通”看到的宇宙情形是怎样的呢?在他书中写道: (5)“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压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
这个叫江希张的“神童”的“天眼通”,和现在一些自称能和“玉皇大帝”、“观世音”交流“宇宙语”的“特异功能者”之类颇有异曲同功之妙。《大千图说》于1916年出版,作者在书中说他“创立三千大千世界之说”,是鉴于“近来物质家,创无天帝鬼神之说,一时靡然从风,不知其贻害之大,将有使全球民物同归于尽者”。他还扬言:要使“天下人人莫不敬天畏天”。这段话,更简直同近年一些新编“气功”的“鼻祖”、“大师”们声称的“到了21世纪世界将毁灭”,只有人人都练他(她)那家气功才会拯救人类的论调如出一辙。
那个“神童”江希张被国内外的守旧势力所广为宣传,美国的李佳白还以“万国道德总会”名义出版了“神童”著的《息战》一书,并为该书写序,称他“具天纵之姿,有卫道之志”,“以一童子而能融洽教理,为世界民族请命”。
所以鲁迅在嘲讽蒋维乔的静坐养生法后,又辛辣地在《杂感•三十三》中写道:“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鲁迅对此作了许多批判。
据说,这个“神童”所谓10岁著书的特异功能都是假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等书都是他父亲江钟秀和别人代写的。(6)
近年来,有人认为有关气功及特异功能的争论只是解放后的事,以上事实说明并非如此,说明早在80年前就有对“伪科学”的批判。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反对静坐养生的并不仅鲁迅一人。《新青年1917年4月1日在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一篇《体育之研究》中就有一段话:
“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即毛泽东。
1920年1月长沙《体育周报》特刊第二号有篇《辟静坐》,更激烈地写道:
“静坐的最大害处,就是使人趋于消极,我们一天天的习静,清心寡欲,就一天一天把进取心消磨了……这样子的静坐,即令能祛病,能延年,也不过替我们中国多造一些人类的寄生虫,和社会的蟊贼……”
如果说毛泽东对“静坐养生”的批判,还主要从运动形式(动和静)出发,这篇《辟静坐》则纯粹把运动方式“无限上纲”到政治批判上,已很像文革时期“火药味”浓浓的“大字报”了。
虽然鲁迅、毛泽东等人都曾反对静坐气功,但中国许多人仍坚持静坐锻炼,当时的一些高等学府还成立师生组成的“静坐会”(相似于如今的健身俱乐部、协会)。静坐法流行不衰,许多提倡新文化的斗士也靠它祛病强身。比如郭沫若,他因年青时治学过勤患严重神经衰弱,形销骨立、夜不能眠,痛苦得几乎自杀。百药无效之时他坚持静坐练功,结果顽疾痊愈。静坐法的奇效使他多次浩叹道:
“从前眼前的世界只是死的平面图、到这时候才活起来,成了立体。”“静坐于修养上是真有功效,我很赞成朋友们静坐。我们以静坐为手段,不以静坐为目的,是与进取主义不相违背的。”(7)
这种见解,比之鲁迅等人偏激批判无疑公允得多。
4.鲁迅反对中国拳术(武术)
鲁迅反对静坐养生的同时,还明确反对另一国粹--中国拳术。原来,当时提倡武术者中,除了众多武术家外,还有许多爱好武术的当权者。如马良(又名马子贞),回族人.民国初年任北洋皖系军阀中陆军第四十七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后任济南镇守使。他甚好武术,自己创编了一套技击术,包括了摔角、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并将其用于军队训练中。马良竭力提倡“国粹体育”,曾说;“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新武术者。”他倡导要将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成“新武术”,使之成为“我国之国粹”。他认为欲使武术发展普及,还应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以发扬武德、武风。当时的北洋政府和一些教育家(如章士钊、蔡元培等)对此很赞赏,将它列入中等以上学校的“体操课程”,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国会还通过了把“新武术”定为全国“学界必学”之“中国式体操”的决议,以利普及,成为教科书。在一些高等学府还成立了武术组织,如北京大学就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倡导支持下成立了“技击会”,师生中参加者甚多。
鲁迅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1918年11月1 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杂感三十七》,以他特有的辛辣笔调嘲讽道:
“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地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
鲁迅很反对“竭力提倡打拳”者认为可将“新武术”用于“体育上”和“军事上”的观点。鲁迅认为;“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验’”。因此他反对将打拳用在“体育上”,嘲讽“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须改习本国式体操(打拳)才行”的说法:“无如竞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拷’那些把戏了”。
鲁迅对打拳可用在“军事上”尤为反感。他又嘲讽道:
“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领袖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种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蠢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 (8)
鲁迅认为“清朝末年(1900年)“满清王公大臣”提倡打拳(如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支持义和团广设拳坛,结果后来是“完全失败了”。更何况“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所以鲁迅反对“打拳”能用在“军事上”的说法。
鲁迅也反对提倡、普及武术这一“国粹”,他在《杂感六十四》上再次尖刻地写道:
“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大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 ‘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桩腿’、‘潭腿’ 、‘戳脚’,什么 ‘新武术’、‘旧武术’,什么 ‘实为尽美尽善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筋力,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 (9)
认为传播中国传统体育武术,是“互害”--鲁迅这一立论今天读来是颇使人吃惊的,无疑很有点偏激、过“左”的味道。
鲁迅对武术界内部的争论更加以嘲讽。山东人王讷(众议院议员)曾提出“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提倡改革武术使之成为中国式体操,此议案于19l7年3月22日经众议院通过,而一些热爱传统武术者(如中华武土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会使武术这一国粹的特色丢失。(本文作者注:这种情况,很像现在“官方武术”如“自选拳”、“国家规定竞赛套路”等与“民间武术”争论的情况。)鲁迅讥讽这是“同业的内讧”:
“但总觉现在时势不很太平,无论新的旧的,都各各起哄:扶乩打拳那些鬼画符的东西,倒也罢了……””北京议员王讷的提议推行新武术,以‘强国强种’;中华武士会便率领了一般天罡拳阴截腿之流,大分冤单,说他抑制暴弃祖性相传之国粹”……(10)
鲁迅对武术这一“国粹”的讥讽反对是否正确呢?这里且先不讨论。只须说出的是,当鲁迅那篇《杂感三十七》一问世,立即有人力加驳斥。驳斥者并非鲁迅讥讽的“那一班”提倡打拳的“教育家”,而是热爱武术的武林中人。5.武术家陈铁生撰文驳斥鲁迅
鲁迅于1918年参加《新青年》的编辑活动并成为重要撰稿人。他在1919年发表《随感三十七》后,《新青年》杂志即收到署名陈铁生的一篇驳斥文章:《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鉴于这个陈铁生是近代武术史上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后文将谈到),而他这篇同大文家鲁迅“打笔墨官司”的文章却极少有人提及,这里全录此文、对研究陈铁生及武术史非常有益。请看原文是怎样驳斥鲁迅的:
现在教育家主持用中国拳术者,我记得有一位蔡子民(即蔡元培)先生,在上海爱国女校演说,他说;“外国的柔软体操可废,而拳术决不可废。”这位老先生,大抵不是满清王公。当时我亦不以为然。后来我年近中旬,因身体早受攻伐,故此三十以后,便至手足半废。为一位医学博士替我医了两三年。他说,“药石之力已穷,除非去学柔软体操。“当时我只可去求人教授。不料学了两年,脚才好些,手又出毛病了;手好些,脚又出毛病。卒之有一位系
原文谓“外国不会打拳”,更是荒谬。这等满清王公大臣,可谓真正刚毅之不如。这一句不必多驳,只可将Boxine(此系西文,是友人数我的。)这几字,说与王公大臣知,便完了。枪炮固然要用,若打仗打到冲锋,这就恐非
粤人陈铁生。八年一月二十日。
“内功”非枪炮打不进之谓,毋强作内行语。铁生赘(11)
这里有必要将陈铁生的驳斥文章略作归纳。
首先,他反对鲁迅把“拳匪”(义和团)弄神搞鬼的“神拳”,同中国传统武术技击混淆起来,而把中国拳术也斥为“鬼道主义”。第二,陈铁生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坚持认为中国拳术“起死回生”的健身功效远胜过西洋体操,故他极赞同蔡元培的话:“(中国)拳术决不可废”。至于中国武术中有些叫法不“雅驯”(不太科学),是因为满清统治者禁武造成的,因而使中国武术在世界体育中“黯然无色”,而仅得中国武术皮毛的日本武士道反大出风头。
第三,陈铁生反对那种认为已有枪炮就可以不要武术技击术的论调,他认为无论中外,打仗冲锋时技击术总是有实战意义的,因而要求鲁迅“毋强作内行语”。
陈铁生的文章是很尖锐的。此时的鲁迅还没有被认为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12)而《新青年》杂志是最提倡民主、学术争鸣的刊物,故陈铁生的文章很快刊登出来。
鲁迅因之在1919年3月2日又写了一篇《拳术与“拳匪”》作公开“答复”:
此信单是呵斥,原意不需答复,本无揭载的必要;但末后用了“激将法”,要求发表,所以便即发表。既然发表,便不免要答复几句了。
来信的最大误解处,是我所批评的是社会现象,现在
其次,对
技击术的“起死回生”和“至尊无上”,我也不能相信。东瀛的“武士道”。是指武士应守约道德,与技击无关。武士单能技击,不守这道德,便是没有武士道。中国近来每与柔术混作一谈,其实是两件事。
美国新出“北拳对打”,亦是情理上能有的事,他们于各国的书,都肯翻译:或者取其所长,或者看看这些人如何思想,如何举动;这是他们的长处,中国一听得本国书籍,间有译了外国文的,便以为定然宝贝,实是大误。
Boxing的确是外国所有的字,但不同中国的打拳;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不会”。正如“拳匪”作Boxer,也是他们本有的字;但不能因有此字,便说外国也有“拳匪”。
陆军中学里,我也曾见他们用厚布包了枪刃,互相击刺,大约确是枪剑术;至于是否逃不出中国技击范围,“外行”实不得而知。但因此可悟打仗冲锋,当在陆军中教练,正不必小学和普通中学都来练习。
总之中国拳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因为这是小事。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作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所以写了这一条随感录,稍能提醒几个中国人,则纵令被骂为“刚毅之不如”,也是毫不介意的事。(13)从以上鲁迅辨解文章中可看出,因为马良写的那本《新武术初级拳脚科》曾经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而且《新武术》序说过一些肯定义和团利用武术的话如:“世界各国,未有愈于中华之新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所以鲁迅就坚持认为”:1.推广武术便的确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正是‘鬼道主义’精神;2.即使拳术可治病健身,却“仍无普及的必要”;3.即使拳术可用于军事,也“当在陆军中教练,正不必小学和普通中学都来练习”。
总之,鲁迅坚持反对“大有中国人非此(指武术)不可之概”——即不应在中国人中宣传、普及武术这一“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