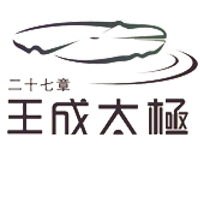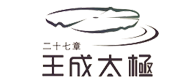(续上期)
编者:上期刊载了作者在北京拜访杨益臣先生胞弟杨德厚先生的谈话记录。
笔者返回西安后,有幸找到了杨益臣的长子杨家琳先生(原西安未央医院院长,已退休)了解到一些情况,家琳先生提供了家谱和《清史稿》的有关记载。限于篇幅,以下仅为部分谈话内容。
杨家琳先生讲:我父亲1928年从师于陈发科公学拳,以后终生练拳,直至病故从未间断。我母亲讲过:北京名医赵炳南学拳于陈发科还是我父亲介绍的,那时我父亲找赵炳南看病,得以相识,后成朋友。赵医生后来讲:“杨益臣一脱了衣服后,看这身腱子肉就知道是练过功夫的人,开刀后皮下没脂肪,都是肌肉”。我父亲和他非常要好,专门介绍他跟陈发科学的陈式太极拳。
1937年日本人发动七七事变,侵华战争打响,北京电报局决定紧急内迁,大家痛恨日本鬼子,都不愿意留下来给日本人做事。父亲的同事张碹,先到的西安,他给父亲写信,说西安安全还不错,叫他们来。那时刘慕三、杨益臣、李鹤年、刘亮等一批人随着设备撤出北京,开始西迁,刘慕三到太原后就被留了下来,就没往下走。在过黄河时,车队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死了很多人,停了下来,刘亮这时染上急病,因医疗条件差,病死了。父亲他们一行渡过黄河,来到了西安。鉴于当时抗战形势,为了安全,西安电报局从城里搬到在长安韦曲离西安城南约十几公里的杜公祠附近。我父亲从1937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一直在那里任报务员工作。
我父亲到西安韦曲后,每天坚持练太极拳从不间断,当地有个庙叫牛头寺,里面有个青年和尚(法号仁义)外号“铁佛”,自幼习武,很有功夫,比较气盛。一日他看到我父亲练拳,他没见过,问练的什么,我父亲说太极拳,他说这也叫拳,要和我父亲试手,没想到一交手就被捋了个大跟头,于是他非要拜我父亲为师。我父亲讲学拳可以,以后可不许惹事,后来大家都称他为“仁义和尚”。 仁义和尚跟着我父亲在韦曲学了好些年,他学的最好,每天练拳一二十遍,一震脚庙里房梁上的土都掉下来,地下的砖都碎了很多,很有功夫,后来庙里主持都不许他在屋里练拳了。

1945年电报局搬回到西安城里,我父亲在莲湖公园练拳,他们单位一些员工和外边的人跟着他学的就很多了。那时西安有很多从河南陈家沟和赵堡镇釆的人,得知我父亲是陈发科的徒弟后,常来请教,当时较有名气的有陈立之、陈熙照、陈敬平等,他们都很敬佩我父亲,多次跟我父亲的学生说过,我父亲拳打得好,到底是陈发科教的,就是不一样。
[NextPage]
我记得1947年的一天,我父亲的几个学生跑到我家讲,说革命公园最近来了个高手,这么些天天与别人推手无人可敌,把不少人都摔得够呛,有人联合起来要找他寻事。我父亲说这不行,我去看看,就带着我和徒弟去革命公园了。远远就看见一群人轮流和一个穿着蓝大褂带着帽子的人推手,我父亲一看这不是“仁义和尚”吗!他什么话也没说,走到仁义和尚背后,咳嗽了一声。仁义一个激灵转过身看见我父亲,规规矩矩低着头喊了声“师傅”。我父亲讲:以后不要到西安来推手了,快回去吧。仁义和尚听罢,什么也没说,给我父亲鞠了个躬,转身就走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他。这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父亲让徒弟都喊他“老师”而不是“师傅”,只有这个仁义和尚例外,我当时还很奇怪。当时与“仁义”推手的人中如铁路上的李尧、屈广斌等后来也跟我父亲学拳了。
陈式太极拳名家第十七世传人陈子明的徒弟马真如随师练陈氏新架(小架)多年,造诣颇深,与我父亲相识后常来家中讨教,往往在推手时被某一招式放出,多次重复而不得其解。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多次讲解,直至马掌握为止。马很感动,介绍他徒弟汤立民拜我父亲为师。汤立民后来成为父亲学生中功夫最好者之一。
我父亲的学生很多,我所知坚持下来练拳的有下列之人:
1938年-1945年期间:
仁义和尚:原西安韦曲牛头寺出家人,外号“铁佛”,姓名及生卒年不详,功夫最好;何慎之:原电报局同事,年轻多病,练拳受益,七几年逝世,享年八十五;张俊:原电报局同事,生卒年不祥,早期随师学拳,后调动去了四川,去后失去联系;朱春荣:原电报局人员,杨益臣的报务徒弟,后随师学拳多年。八十年代逝世。
1946年-1960年期间:
李尊尧:河南人,1945年学拳,五几年病故(生卒年不详);张万生:陕西西安人 (1928年-2007年);樊鹤云:河南孟县人(1930-不详);白悦本:河南温县人(1929-2007),随师学拳较长,授徒最多;汤立民:河南孟县人(1930-至今),功夫最好;司马国柱:河南温县人(1928-至今),年轻时体弱,练拳受益,至今仍每天练拳健身。
以上为杨益臣长子杨家琳先生听提供的情况。笔者接着又对仍健在的杨益臣徒弟汤立民、司马国柱两位老先生进行了多次采访。
据司马国柱和汤立民两位先生讲:我们和白悦本师兄弟三人从1946年开始,在莲湖公园跟先生陆续学拳的(其中以汤立民功夫最好,白悦本随老师较长,弟子最多)。此前在韦曲就有人跟先生学拳,听先生讲:其中“仁义和尚”学拳最好,是带艺来学拳的,学陈氏太极拳时,非常用功,一天练拳二三十遍,长年如此。

先生搬到到西安后,开始是在莲湖公园西门处练拳,每天天不亮人就到了。我们刚学拳时,听公园看门人讲:“你们师傅厉害,我每天早早起来扫地,公园没一个人,如果听见西门处‘通通’声音和‘呼呼’的风响就知道你们师父来了”。后来我们发现不论去多早,先生拳都练完了,我们问:“先生您怎么起的那么早”?先生讲:“这还早,我当年学拳时,这个点陈发科老师拳都练完了,你们要用功呀”。
在莲湖公园最早是电报局的一些人跟他学拳,其中一个姓何的师兄练得较好,年龄也长我们很多,他开始时都教过我们。他原来身体很差,通过练拳后把身体练好了,活了85岁,七几年才不在了。
我们先生的人品是没说的,他在西安教拳多年,推手就没输过,人们都知道他厉害,四十年代,武行中提起杨二爷可是无人不晓。可他跟别人试手,都是点到为止,很给别人留面子,从来没有打过人,武行人说起他都竖大拇指。
四几年后有很多陈家沟、赵堡镇的人逃难来西安,当时城西头陈姓几兄弟拳打得很有名,他们听说先生是陈发科的徒弟。就想见见他的拳,常向他讨教。我们后来讲:“先生怎么不跟他们推一下,让他们知道咱们拳的厉害”,先生严肃批评我们:“这像话吗?我的拳是跟人家陈家学来的,你怎好意思去推人家,还有没有德行!”。
我们跟老师学拳时间不久,一天有一位白姓老师(练吴式太极拳在西安很有名气),来找先生推手玩,我们看先生光用“云手”粘住对方,推得极快,白师傅步子跌跌跄跄跟不上。平时老师绐我们示范时发劲极脆,我们一挨上,人就出去了,就这样老师都没摔对方一下。送走白先生后,老师讲:“你们看清楚了没有,云手不光能慢,快了也能粘得住。你们练拳不能打人,要讲武德”。
先生跟郑梧清老师也见过面,都很尊重对方说“久仰、久仰”,两人搭了一下手臂,就松开了,互相都说你的拳好,功夫深,大有相见恨晚的样子。没有一点门派见识,武德是真好哇。

那时,我们家里都比较困难,跟老师学拳时,老师没收我们一分钱,我们很过意不去,当时老师家那边的井水不好、发苦。我们就常帮着老师家从外边挑水,可是每次师母都留我们吃饭,我们很感到过意不去。一次过年时,我们请老师吃饭,饭后大家都争着付账,老师讲:“你们谁也不许付账,我来付。今天给大家立个规矩,以后大家一起吃饭各人付各人。“现在我一想起这事心里就热乎乎的,想想老师无私免费教拳。从不藏掖,请老师吃个饭都不叫我们掏钱,老师的品行真叫我们今天的人感到汗颜呀。
司马国柱1950年回老家温县老家结婚,还专程到陈家沟看陈照旭先生,并求教陈照旭老师捏拳架,陈老师让司马国柱走完架子后说,架子不用捏了,你老师当年学的最好,走的老架子和我父亲一样,他要是不对就没人对了,你就是松的不够,回去要下苦功练。
解放初,陈照旭来西安时,我们在先生家都见过陈老师,我们现在拳中的“三换掌”就是他教我们加上的,当时,先生叫汤立民练一遍拳给陈照旭老师看,他说先生教的不错,叫我们好好跟老师学,我给你们拳里增加个“三换掌”,这是我父亲后来加上的,教给你们。还跟汤立民搭了一下手,说功夫还不够,要好好练。
1964年陈发科公的徒弟王雁(字庭选)来西安时,得知我们是杨益臣的学生,还专门给白悦本捏拳,传授技法。
70年代末,陈小旺、陈正雷、王西安等先生都来过西安拜访过我们。
很不幸,1960年先生就因病逝去。我们跟先生学拳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受到的教诲是终身难忘的。我们跟老师学拳不仅强健身体,更主要跟老师学会要怎样做人。几十年来,我们师兄弟之间,牢记先生的嘱托,互帮互助,虽不同姓,却亲如一家人。我们后来教徒弟,都是按先生的要求去做的。先学做人,再说学拳,先健身,再防身。万不可逞强斗狠,任何时候要牢记武德和人品是最重要的。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笔者还曾对下列人员:白悦本长子白长兴、白悦本学生任艳琪、李世俊、杨艳武、刘宝欢、陈发科弟子李鹤年的徒弟闫海峰、曹臻、项如元、李霖(李鹤年之子、、杨益臣好友张宣的徒弟任建明、包增敏等人进行过采访。在此对他们提供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